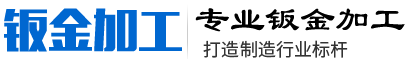HASH GAME - Online Skill Game GET 300

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线)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进入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开始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工。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时期,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秦汉时期(前221-公元220)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系统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未病”和疾病治疗的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温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概括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药物配伍和药性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用药、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西晋时期(265-317),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系统论述了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初步形成了经络、针灸理论。唐代(618-907),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明代(1368-1644),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部药物学和博物学巨著。清代(1644-1911),叶天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温疫(传染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清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
中医药发祥于中华大地,在不断汲取世界文明成果、丰富发展自己的同时,也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早在秦汉时期,中医药就传播到周边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传统医药产生重大影响。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在明清时代就传遍世界。《本草纲目》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达尔文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针灸的神奇疗效引发全球持续的“针灸热”。抗疟药物“青蒿素”的发明,拯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同时,乳香、没药等南药的广泛引进,丰富了中医药的治疗手段。
中国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把“团结中西医”作为三大卫生工作方针之一,确立了中医药应有的地位和作用。1978年,中央转发卫生部《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并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保护人民健康。1986年,国务院成立相对独立的中医药管理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中医药管理机构,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将“中西医并重”列为新时期中国卫生工作五大方针之一。200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200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医药政策体系。
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和政府把发展中医药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强调,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医药法(草案)》,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制保障。2016年,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作为今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振兴中医药发展、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任务和举措。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新时期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这些决策部署,描绘了全面振兴中医药、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构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医药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坚持统筹兼顾,推进中医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实施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健全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开展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构建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协同创新体系。实施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人才工程,提升中医药人才队伍素质。推动中药全产业链绿色发展,大力发展非药物疗法。推动中医药产业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弘扬中医药核心价值理念。
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在城市,形成以中医(民族医、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类门诊部和诊所以及综合医院中医类临床科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主的城市中医医疗服务网络。在农村,形成由县级中医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临床科室、乡镇卫生院中医科和村卫生室为主的农村中医医疗服务网络,提供基本中医医疗预防保健服务。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有中医类医院3966所,其中民族医医院253所,中西医结合医院446所。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45.2万人(含民族医医师、中西医结合医师)。中医类门诊部、诊所42528个,其中民族医门诊部、诊所550个,中西医结合门诊部、诊所7706个。2015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1亿,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2691.5万人。中医药除在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的防治中贡献力量外,在重大疫情防治和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疗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肯定。中医治疗甲型H1N1流感,取得良好效果,成果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同时,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手足口病、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传染病,以及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都发挥了独特作用。
中医药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临床疗效确切、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方式灵活、费用相对低廉的特色优势,放大了医改的惠民效果,丰富了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内涵。中医药以较低的投入,提供了与资源份额相比较高的服务份额,2009年至2015年,中医类医疗机构诊疗服务量占医疗服务总量由14.3%上升到15.7%。2015年,公立中医类医院比公立医院门诊次均费用低11.5%,住院人均费用低24%。
建立起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把人才培养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根本,大力发展中医药教育,基本形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有机衔接,师承教育贯穿始终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建立社区、农村基层中医药实用型人才培养机制,实现从中高职、本科、硕士到博士的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民族医药等多层次、多学科、多元化教育全覆盖。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有高等中医药院校42所(其中独立设置的本科中医药院校25所),200余所高等西医药院校或非医药院校设置中医药专业,在校学生总数达75.2万人。实施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人才工程,开展第五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建设了1016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200个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为64个中医学术流派建立传承工作室。开展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中药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培训、乡村医生中医药知识技能培训等高层次和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项目。124名中医药传承博士后正在出站考核。探索建立引导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褒奖机制,开展了两届国医大师评选,60位从事中医药、民族医药工作的老专家获得“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中医药科学研究取得积极进展。组织开展16个国家级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及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临床科研体系建设,建立了涵盖中医药各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室和科研实验室,建设了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形成了以独立中医药科研机构、中医药大学、省级以上中医医院为研究主体,综合性大学、综合医院、中药企业等参与的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近年来,有45项中医药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其中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荣获2011年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和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因将传统中药的砷剂与西药结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疗效明显提高,王振义、陈竺获得第七届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开展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并初步建成由1个中心平台、28个省级中心、65个监测站组成的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以及16个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和2个种质资源库。组织开展民族医药文献整理与适宜技术筛选推广工作,涉及150部重要民族医药文献、140项适宜技术。这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为提高临床疗效、保障中药质量、促进中药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支撑。
中药产业快速发展。颁布实施一系列加强野生中药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一批国家级或地方性的自然保护区,开展珍稀濒危中药资源保护研究,部分紧缺或濒危资源已实现人工生产或野生抚育。基本建立了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突出中医药特色、强调临床实践基础、鼓励创新的中药注册管理制度。目前,国产中药民族药约有6万个药品批准文号。全国有2088家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的制药企业生产中成药,中药已从丸、散、膏、丹等传统剂型,发展到现在的滴丸、片剂、膜剂、胶囊等40多种剂型,中药产品生产工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基本建立了以药材生产为基础、工业为主体、商业为纽带的现代中药产业体系。2015年中药工业总产值7866亿元,占医药产业规模的28.55%,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药材种植成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改善、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中药产品贸易额保持较快增长,2015年中药出口额达37.2亿美元,显示出巨大的海外市场发展潜力。中药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
中医药文化建设迈出新步伐。中国政府重视和保护中医药的文化价值,积极推进中医药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已有130个中医药类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医针灸”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加强中医药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持续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活动,利用各种媒介和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向公众讲授中医药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全社会利用中医药进行自我保健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促进了公众健康素养提高。
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制定实施《中医药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医药标准体系初步形成,标准数量达649项,年平均增长率29%。中医、针灸、中药、中西医结合、中药材种子种苗5个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广东、上海、甘肃等地方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相继成立。42家中医药标准研究推广基地建设稳步推进,常见病中医诊疗指南和针灸治疗指南临床应用良好。民族医药标准化工作不断推进,常见病诊疗指南的研制有序开展,14项维医诊疗指南和疗效评价标准率先发布,首个地方藏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西藏自治区成立,民族医药机构和人员的标准化工作能力不断提高。
推动中医药全球发展。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中药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系,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总部设在中国的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有53个国家和地区的194个会员团体,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有67个国家和地区的251个会员团体。中医药已成为中国与东盟、欧盟、非洲、中东欧等地区和组织卫生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与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支持国际传统医药发展。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国际传统医药发展,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密切合作,为全球传统医学发展作出贡献。中国总结和贡献发展中医药的实践经验,为世界卫生组织于2008年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首届传统医学大会并形成《北京宣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政府的倡议下,第62届、67届世界卫生大会两次通过《传统医学决议》,并敦促成员国实施《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年)》。目前,中国政府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中医药合作协议86个,中国政府已经支持在海外建立了10个中医药中心。
开展中医药对外援助。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国际义务。目前,中国已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70多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基本上每个医疗队中都有中医药人员,约占医务人员总数的10%。在非洲国家启动建设中国中医中心,在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马耳他、等国家还设有专门的中医医疗队(点)。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在海外支持建立了10个中医药中心。近年来,中国加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开展艾滋病、疟疾等疾病防治,先后派出中医技术人员400余名,分赴坦桑尼亚、科摩罗、印度尼西亚等40多个国家。援外医疗队采用中药、针灸、推拿以及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了不少疑难重症,挽救了许多垂危病人的生命,得到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充分肯定。
中国将学习借鉴各种现代文明成果,坚持古为今用,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切实把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服务于人民健康,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同时,积极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促进中医药等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探索医疗卫生保健的新模式,服务于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